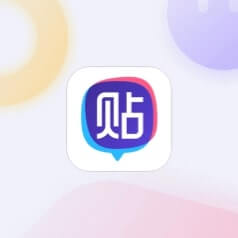她那一缕叹息化作碧痕,凝在了我的剑上。
三个月后,我决战于昆仑山顶,剑光照雪,艳梅飘花。
我回来了,他死了。
我走进他的家里,什么也没有说。
她说:“你等等我。”然后悄悄走进了屋里。
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师妹,我只看见丫鬟送上的长剑,剑上有隐隐的血痕。后来我带她的灰回到小镇,埋在师傅的脚下。
那柄剑则成为我的配剑,叫“过去”。
真的,直到今天想起来我依然觉得小师妹不是因为我而死的,那是因为偶然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比较唯物,我会说那是宿命的缘故。
每个少年都想顶天立地,练最强最强的武功,当最大最大的大侠,我也一直以为当年的作为没有错。我走出了那个小镇,我去拼杀,我当天下第一。
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天下第一不是靠我流血换来的,而是靠我的牺牲。这个词听起来很吓人,我只是说,我牺牲了其他东西,换来了天下第一。比如,我再也见不到小师妹,我再也不适合那个小镇,一万两银子再也激不起我的兴趣。
当然我也得到了点东西,比如“天下第一”。
天下第一是个好东西,不过当我现在站在水之阳看风景的时候,我觉得有点无聊。
我不后悔,可是我已经累了。当年那条河流我已经踏了进去,现在脚下的河流还在奔流——没有回头。
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
夕阳照在我的头顶,江上烟波碎。
“各位客官,去北口的船,还有一个位子,有人上么?”渡口的梢公破锣一样的嗓子响起。
我忽然一惊,北口的方向去向我的家。
“还有一个人,有人上么?”
“还有位子,有人上么?”
“没人上么?”
……
……
“没人上开船了!”
忽然间我跑了起来,梢公听见了身后比他更加破锣的声音:“别走啊,有人呢,有人呢!”
就这样,我现在静静的挤在了船舱的小角落里,一边看着夕阳,一边飘在江上。江风吹啊江风吹,我喝着一瓶劣酒,隐约觉得那风一定从我们镇子上过,里面还有栀子花和牛肉面的味道。
我要回家了,去买栀子花,吃牛肉面,看老七的婆娘,如果说得高雅点,我想听那脚步的诗。
我开始高兴的哼小曲。
我现在更加认定那个西域大胡子是随口骗我的。
哪有哲学家那么不严谨?不错,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,不过永远有河流在你面前,你想怎么踏怎么踏就是了。我现在想回去。
为什么回去?
因为我累了吧?嗯,也许,反正是江湖上我不想玩了,那么我就回头大踏一步。
水花溅在我的脸上,我对自己说我不后悔,只是觉得可以再选择一次。
想到我等待的那个弟子来到码头,发现再也找不到我而左顾右盼的样子,我就高兴的要笑起来。
让我们荡起双浆,小船儿轻轻飘荡……
三个月后,我决战于昆仑山顶,剑光照雪,艳梅飘花。
我回来了,他死了。
我走进他的家里,什么也没有说。
她说:“你等等我。”然后悄悄走进了屋里。
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师妹,我只看见丫鬟送上的长剑,剑上有隐隐的血痕。后来我带她的灰回到小镇,埋在师傅的脚下。
那柄剑则成为我的配剑,叫“过去”。
真的,直到今天想起来我依然觉得小师妹不是因为我而死的,那是因为偶然。如果不是因为我比较唯物,我会说那是宿命的缘故。
每个少年都想顶天立地,练最强最强的武功,当最大最大的大侠,我也一直以为当年的作为没有错。我走出了那个小镇,我去拼杀,我当天下第一。
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天下第一不是靠我流血换来的,而是靠我的牺牲。这个词听起来很吓人,我只是说,我牺牲了其他东西,换来了天下第一。比如,我再也见不到小师妹,我再也不适合那个小镇,一万两银子再也激不起我的兴趣。
当然我也得到了点东西,比如“天下第一”。
天下第一是个好东西,不过当我现在站在水之阳看风景的时候,我觉得有点无聊。
我不后悔,可是我已经累了。当年那条河流我已经踏了进去,现在脚下的河流还在奔流——没有回头。
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
夕阳照在我的头顶,江上烟波碎。
“各位客官,去北口的船,还有一个位子,有人上么?”渡口的梢公破锣一样的嗓子响起。
我忽然一惊,北口的方向去向我的家。
“还有一个人,有人上么?”
“还有位子,有人上么?”
“没人上么?”
……
……
“没人上开船了!”
忽然间我跑了起来,梢公听见了身后比他更加破锣的声音:“别走啊,有人呢,有人呢!”
就这样,我现在静静的挤在了船舱的小角落里,一边看着夕阳,一边飘在江上。江风吹啊江风吹,我喝着一瓶劣酒,隐约觉得那风一定从我们镇子上过,里面还有栀子花和牛肉面的味道。
我要回家了,去买栀子花,吃牛肉面,看老七的婆娘,如果说得高雅点,我想听那脚步的诗。
我开始高兴的哼小曲。
我现在更加认定那个西域大胡子是随口骗我的。
哪有哲学家那么不严谨?不错,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,不过永远有河流在你面前,你想怎么踏怎么踏就是了。我现在想回去。
为什么回去?
因为我累了吧?嗯,也许,反正是江湖上我不想玩了,那么我就回头大踏一步。
水花溅在我的脸上,我对自己说我不后悔,只是觉得可以再选择一次。
想到我等待的那个弟子来到码头,发现再也找不到我而左顾右盼的样子,我就高兴的要笑起来。
让我们荡起双浆,小船儿轻轻飘荡……